
现今,在我的家乡大同的中老年人当中仍然流传着这样一种民俗,就是把打喷嚏看作是有人在“说”的征兆。见别人打喷嚏,则打趣道:“肯定您老婆说您呢!”自己打了喷嚏,则纳罕道:“谁又说我呢?”这里的“说”本意是谈论、提及的意思,后来又引申出褒贬二义,褒义为挂念,关心;贬义为议论,讥谤。总之是说,凡打喷嚏,一定是此刻有人在什么地方提到了他。昔日敝乡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某甲乙二人搭伴儿卖瓦盆,一日某甲连打二嚏,某乙羡曰:看,一定是人家老婆在家说呢!次日某甲又打数嚏,某乙羡煞,回家即抱怨妻子道:某甲老婆多关心,人家一路尽打喷嚏!我呢,从来也没人挂念过!某乙妻子笑曰,明日我亦当好好关心关心你,遂交某乙一手帕以供揩鼻之用。果然,次日途中某乙每用手帕后都喷嚏连连,打了喷嚏又须用手帕去擦鼻子,于是又是一连串喷嚏。由于喷嚏不止,至过桥时竟至将一担子瓦盆打碎并掉入河中,某乙气愤道:看我这个老婆,要不是不关心,要不就关心个没完!原来,某乙妻所交某乙之手帕蘸过胡椒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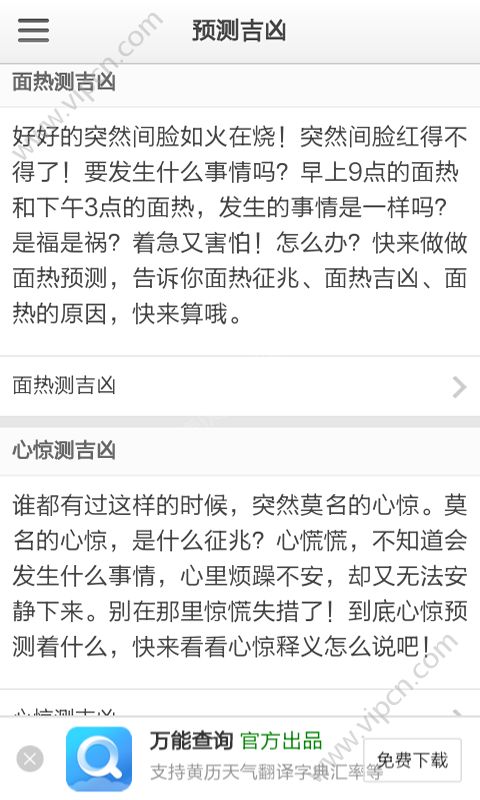
其实,打喷嚏为有人“说”的民俗既不限于大同一带,亦非仅近代流传,其流行范围极广,流传时代极早,可称是源渊流长了。早在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中就有关于喷嚏的诗句,《邶风》中《终风》一诗,有这样一句:“寤言不寐,愿言则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笺注道:“俗人嚏,云‘人道我’。”严粲《诗缉》中亦释曰:“愿其嚏而知己念之也。”宋人马永卿为此说觅证,于其大作《懒真子》中说:“《汉艺文志》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内嚏、耳鸣杂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计反。然则嚏、耳鸣皆有吉凶,今则此术亡矣。”可知这种民俗一度还衍化为占卜术。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解释,比如清儒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斥郑玄之说为“穿凿之见”。当代学界巨擘钱钟书先生也表示不同意郑说,但他却从另一个角度看到郑《笺》这段注释的民俗价值,《管锥编·毛诗正义·旄丘》中说:“就解《诗》而论,固属妄凿,然观物态、考风俗者有所取材焉。”所见极是。起码我们可以通过郑《笺》据知这种民俗至晚在郑玄生活的东汉时期已经颇为流行了。
在以后的许多笔记和文艺作品中,也常常可以见到有关的描写。比如明代冯梦龙评点的《挂枝儿》中,就有一曲专名《喷嚏》,其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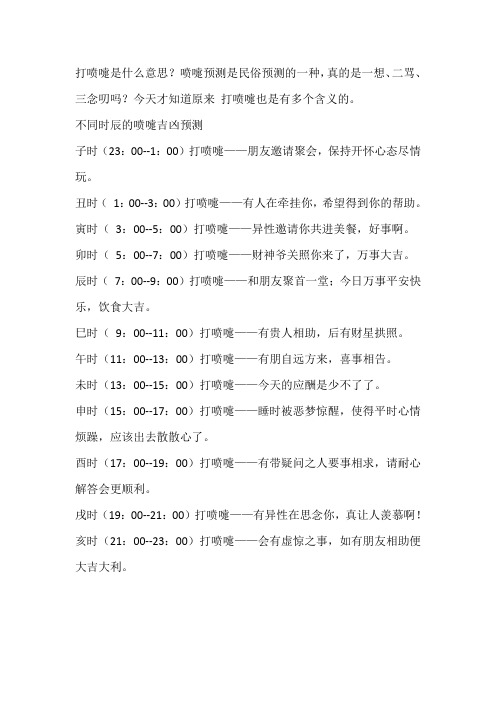
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自从别了你,日日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常似雨。


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前半截说一个痴心女子因自己打了个喷嚏,便忖度是“情哥”思量自己而寄来的“信儿”;后半截又由此推想:如果喷嚏真得这么灵验,那么象自己这样朝朝暮暮地思念情哥,他一定是喷嚏如雨了。这段小曲的作者叫遐周,大约是冯梦龙的朋友或相识,冯梦龙在评语中曰:“‘愿言则嚏’,一发于诗人,再发于遐周。遂使无情之人民俗杂占喷嚏,喷嚏亦不许打一个。可以人而无情乎哉!”确实,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只曲子的创作受到《诗经》的影响,冯梦龙所谓的“诗人”,不是今天白话文意义上的泛指,而是专指《诗经》的作者。第二首与喷嚏有关的曲子叫《查问》,其二曰:
负心人,这几日你在谁家睡?风月中,哪有你这样薄幸贼!教奴念得舌尖儿碎。你难道喷嚏儿也不打一个,耳朵儿也不热一回?实实的招来也,冤家,莫讨费了嘴!
这也是借一个青楼女子的声口写出的一只曲子,是对“情哥”的嗔怪,质问他对自己的叨念是不是有所反应。这只曲子不光说到喷嚏,还说到了别一种与此极为相似的民俗:耳热。民间百姓多认为民俗杂占喷嚏,有人念叨会引起耳热。这与喷嚏为有人“说”,完全同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