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
[英]杰夫·戴尔 著
叶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一部关于D.H.劳伦斯的非学术著作。它既像传记又不是传记,既像小说又不是小说,既像游记又不是游记,既像回忆录又不是回忆录:一种融合,或者说,超越了所有特定文体的后现代文体,一种反文体的文体。所以,虽然作者一再声称要写一部“研究劳伦斯的严肃学术著作”,但最终却写成了一部既不严肃也不学术,而且让人从头笑到尾的黑色喜剧。它仍然是关于劳伦斯的,不过更准确地说,是关于“想写一部关于劳伦斯的书却没有写成的书”。尽管如此,作者还是用他那自由自在的新文体,用如香料股遍洒在文本中的对劳伦斯作品的摘录、描述和评论,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独特的D.H.劳伦斯。我们从中得到的不是一个伟大作家干瘪的木乃伊,而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种感觉,一种精神——一阵裹挟着劳伦斯灵魂的风。
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简直难以相信我已经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才要去开始对 D.H.劳伦斯的研究;另一方面几乎同样让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曾经开始过这项研究,但由于着手这个工作而加速引发了我的精神紊乱症,只得暂停下来待情绪得到缓解。说到分散注意力,马上就会想到需要某种能够分散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注意力,换句话说就是我自己。如果,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可以让自己保持冷静——我记得自己反复对自己说“冷静”,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需要拉响精神错乱的警铃——如果我可以让自己保持冷静,那么,进行对 D.H.劳伦斯的学术研究将会迫使我振作起来。我成功地让自己专注,但所专注的事项——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现在我已经迷失在远离原本预期的严肃的学术研究中了——将是要对这本书大加批评一通,而这本书,原本是要让我振作起来的。
多年前我就决心将来要写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书,向这位让我想成为作家的作家致敬。这是个非同一般的野心,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要做些准备的我于是避免阅读劳伦斯写的任何东西,这样的话等将来研究他的时候即使不是全新的也至少不会太陈腐。我不想消极被动地去研究他,不想无目的地照抄《儿子与情人》来打发时间。我想有目的地去读他。于是,经过几年的逃避劳伦斯,我进入了可以称其为预前准备的阶段。我拜访了伊斯特伍德,他的出生地,我读了传记,我攒了一堆照片,把它们放在曾是全新的文件夹里,蓝色的,上面用黑色的墨水毅然决然地写着“D.H.劳伦斯:照片”。我甚至做了惊人的一叠关于脑海里模糊的劳伦斯印象的笔记,但这些笔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显然,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是准备和促进这本书的写作讲述人物传记的小说,而是在推迟和拖延写作。这一点也不奇怪。全世界的人都在把做笔记当作推迟、延期和替代的理由。我的情况更为极端,因为做关于劳伦斯的笔记不仅仅是在推迟写一本有关某位作家的学术研究———向其致敬——是这位作家使我想成为作家,而是我在拖延的这个研究本身就是在推迟和拖延另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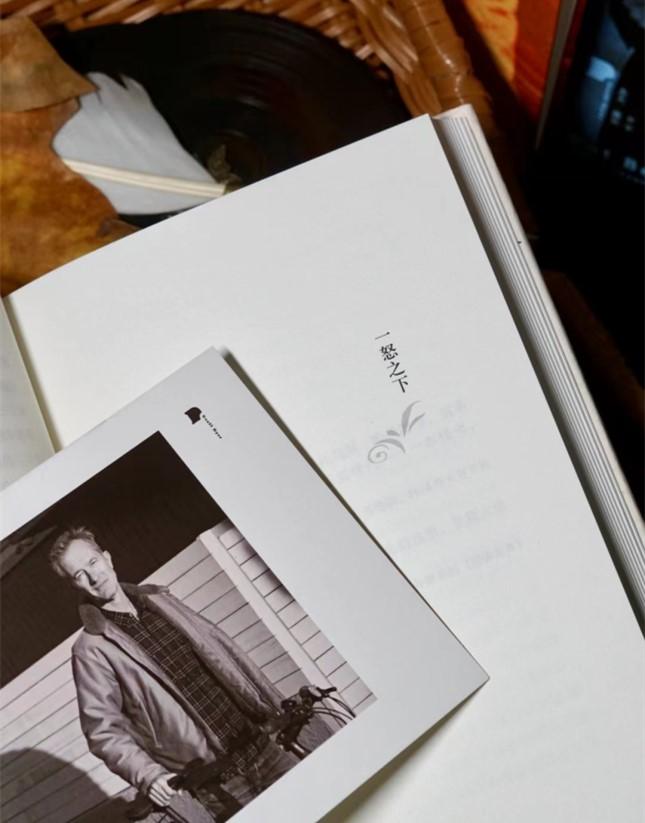
虽然我决定要写本关于劳伦斯的书,但同时也决定要写本小说,当稍后做出决定要写本关于劳伦斯的书时,这个决定并没有取代之前的决定。最初,我迫切地想要同时写这两本书,但这两股欲望互相拉扯,到最后哪本我都不想写了。同时写两本书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两个气势相当的雄心从最初的相互折磨消耗成了最后的精疲力竭。我只要一想到动手写小说就忍不住想写劳伦斯的研究也许会更愉快些。我一开始做关于劳伦斯的笔记便意识到自己可能在永久性地蓄意破坏写这本小说的机会讲述人物传记的小说,它比以往我写过的任何一本书都重要,必须立刻动手写,赶在其他可能会突然冒出的事情横在我与灵感之间———所谓灵感,我的理解就是类似本哈德式的漫无目的的夸夸其谈——的前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我从做关于劳伦斯的笔记转为做小说的笔记,我的意思是从不写劳伦斯的书转为不写小说,因为所有这些反复和做笔记实际上都意味着我两本书哪本也没写。最终,我所做的就是在两个电脑文件夹——空文件夹——之间犹疑不定,一个文件夹叫 C:\DHL(劳伦斯的全名缩写),另一个叫 C:\NOVEL(小说), 在被它们像打乒乓一样来回纠结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不得不合上电脑,因为我知道,最糟的就是像这样把自己拖垮。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平静地坐着。当然,不可能平静:相反,我感到彻骨的悲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什么都写不出,不管是劳伦斯还是小说。
最后,当我忍无可忍时,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劳伦斯的研究中。因为小说会让我更接近自我,而劳伦斯——一本关于劳伦斯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则相反,将会带领我摆脱自我。

杰夫·戴尔,被《每日电讯报》称为“很可能是当今最好的英国作家”。他的写作风格极其独特,涉及音乐、摄影、电影等多个领域,并将小说、游记、传记、评论、回忆录等体裁融为一体,形成了奇异而迷人的“杰夫·戴尔文体”。《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