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是对鼓楼西剧场六年历程的个人观察总结,以剧目生产为主,兼及其他方面。动笔前,笔者并未意识到,短短六年,竟足以让人产生恍如隔世之感。出于对戏剧史的兴趣,笔者深知进入不曾亲历的历史有多困难。鼓楼西一路走来,笔者算是个见证者。此番记录,不敢奢求以鼓楼西的发展变化作为切入点,进而透视中国戏剧的整体变迁,惟愿若干年后有人追溯这段往事时,可有今人的切身体会以资参考。
2020年4月,北京鼓楼西剧场(下简称“鼓楼西”)度过了六周岁生日。考察一家如此年轻的民营剧场的发展历程,有必要回溯到鼓楼西成立的2014年。其原因在于:首先,当时的戏剧环境对于鼓楼西的剧目选择和市场策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时至今日,鼓楼西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发轫之初的经营理念;其次,随着戏剧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鼓楼西也在不断与时俱进,调整自我定位和建设思路,对2014—2020年的历时性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家“小剧场”与“大时代”之间的紧密互动。
回望2014年的中国戏剧,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令人记忆犹新,至今还会不时被提及:其一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雷雨》学生公益场演出时,观众频频笑场;其二是罗伯特·威尔逊演出《克拉普的最后碟带》过程中,被观众粗口问候。这两件事都在戏剧行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前者更是成为文化界乃至全社会的舆论焦点。《雷雨》的笑场打破了陈腐僵化的戏剧美学最后的“歌舞升平”──观众的哄笑声针对的并非某场特定演出(《雷雨》随后南下上海的演出发生笑场)、某个特定剧目(北京人艺此前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发生笑场)、某个特定剧院(我于2013年10月2日观看的天津人艺演出的《雷雨》,同样发生笑场),而是一整套名为“现实主义”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生活现实的演剧模式。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北京人艺《雷雨》的价值辩护,但一部分观众的审美倾向正在与恪守传统的艺术追求渐行渐远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再视若无睹。
对罗伯特·威尔逊的谩骂则体现出一种尚未做好准备迎接外国戏剧大规模来华的心理状态。与之前几年相比,2014年在中国上演的外国剧目,数量激增,质量飞跃。在新时期戏剧“二度西潮”[1]的进程中,2014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年,国内最重要的戏剧活动当属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在北京盛大举办,大名鼎鼎的特尔佐布罗斯、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留比莫夫、尤金尼奥·巴尔巴等大师级导演的作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轮番上演,一时间,追星看戏如同过年赶集般热闹非凡。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也在暌违一年后重磅回归,德国邵宾纳剧院的《朱莉小姐》引发业界热议,日后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并与中国戏剧人深度合作的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第一次把作品带到了中国。此后,林展规模不断扩张,至2017年达到顶峰。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戏剧舞台共上演海外剧目近100部,来中国参与演出的海外剧团多达80 余家”[2]。微这些剧目在让中国戏剧人大饱眼福的同时,也留下了些许困惑,更对一些观众的审美习惯构成挑战。
“《雷雨》笑场”与“威尔逊被骂”,两件事同于2014年发生,为我们勾勒出当年中国戏剧版图的大致样貌──一边是某些陈旧传统的难以为继,另一边是“开眼看世界”后大量新鲜事物的有待消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鼓楼西剧场诞生了。
鼓楼西的诞生,恰逢其时。
01
西方当代经典:从“直面戏剧”的标签说起
截至目前,鼓楼西一共制作出品了十三部戏[3]。其中十部外国戏里,《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审查者》毫无疑问属于阿莱克斯·西尔兹(Aleks Sierz)经由《直面戏剧:英国戏剧的今天》(In-yer-face : Drama Today)一书命名的“直面戏剧”。《那年我学开车》也明显带有直面戏剧的艺术特征──“台词粗俗肮脏,动作暴烈卑下,赤裸裸的色情与暴力;人物乖张,情节平淡且荒谬;观众被置于残暴、血腥、恐惧、恶心、焦虑相混杂的压抑情境之中,忍受力达到了极限等等”[4]。以上四部作品,除《审查者》因有关部门的介入只演出了十几场,《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那年我学开车》均为鼓楼西早期作品,是鼓楼西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相比同期的其他自制戏,艺术上更为成功,社会反响也更大。因此,“直面戏剧”成了鼓楼西重要的身份标签。以至于,鼓楼西后来制作的一些剧目,只是与直面戏剧有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却也被含糊笼统地贴上了“直面”的标签。
(《枕头人》2020年演出海报)

(《丽南山的美人》2020年演出海报)
对于“直面戏剧”的标签,鼓楼西欣然接受。在剧场的官方宣传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对作品“直面”属性的突出强调,如把《丽南山的美人》《那年我学开车》《山羊》(因故未能上演)称作鼓楼西“直面戏剧三部曲”。2018年,鼓楼西还推出过“直面戏剧套票”,将《那年我学开车》《枕头人》《晚安,妈妈》《婚姻情境》《丽南山的美人》打包售票。虽然《晚安,妈妈》和《婚姻情境》有着与直面戏剧类似的残酷色彩,但艺术手法与直面戏剧十分不同,将其简单粗暴地划归为直面戏剧,缺乏足够的学理依据。鼓楼西的营销手段扩大了直面戏剧的概念范围,说明剧场主动把“直面戏剧”作为自身品牌建设的一部分。
在直面戏剧成就了鼓楼西的同时,鼓楼西也促进了“直面戏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推广普及。鼓楼西演出直面戏剧,使用的译本均出自戏剧翻译家胡开奇之手,正是胡开奇最早把in-yer-face 译作“直面戏剧”。除“直面戏剧”外,in-yer-face 还曾被译为“无法回避的戏剧”“对峙戏剧”“扑面戏剧”“‘去你的’剧场”。[5]目前,“直面戏剧”已成为最通行的译法,这与鼓楼西的剧目排演和大力宣传不无关系。
显然,直面戏剧是鼓楼西迅速站稳脚跟、确立业界地位的重要原因,并且至今仍是鼓楼西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那么,鼓楼西为什么会选中直面戏剧?又为什么能依靠直面戏剧取得成功?这两个问题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鼓楼西主打直面戏剧,既有偶然因素,也蕴含着一定的必然性;看似出自剧场方面的主观选择,背后却有着客观规律的作用。鼓楼西创始人李羊朵以外行身份闯入戏剧行业时,对戏剧艺术,尤其是戏剧文学的了解尚不足够。在剧场筹备创立的过程中,万方(作家)、李静(评论家、作家)、赵立新(演员、导演)、周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导演)等专业人士提供的意见,深刻影响了鼓楼西艺术方向的选择。当时,赵立新向李羊朵推荐了若干个剧本,李羊朵选中了《山羊》和《枕头人》,《枕头人》先于《山羊》通过演出报批。可以想象,如果当初鼓楼西的开幕大戏是《山羊》而非《枕头人》,或许就不会与直面戏剧如此深度“绑定”。
但我们也不必过高估计变更开幕戏可能造成的影响。原因在于,无论《山羊》还是《枕头人》,都属于西方当代戏剧经典的范畴。不妨再来回顾一下鼓楼西成立前夕的戏剧市场,在北京,引进剧目之外,西方当代经典的排演少之又少。北京人艺和中国国家话剧院作为实力雄厚的国有院团,理应成为排演西方当代经典的主力军。然而,2011—2013年间,这两家剧院的新排剧目中,写作于1980年之后的西方剧作,就只有《打造蓝色》和《明枪暗箭》[6](如果算上改编作品的话,还有改编自电影《烈日灼人》的《深度灼伤》、改编自略萨同名小说的《坏女孩的恶作剧》)。毋庸置疑,西方当代经典的缺席不利于戏剧市场的繁荣和多元发展,“二度西潮”的背景之下,高水平的本土制作更显得迫在眉睫。鼓楼西以直面戏剧开路,带有偶然因素,但踏上一条排演西方当代戏剧经典的“坦途”,却是填补空白后的必然结果。
按照比较文学的观点,“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7]。追问直面戏剧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有必要考察一番,当直面戏剧漂洋过海,于鼓楼西的舞台上演时,是否有些思想内涵和文化趣味被悄然改写?“开业第一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鼓楼西的观众有70%都是90后”[8],是什么吸引着这些年轻人走进剧场?直面戏剧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情感体验?
关于直面戏剧兴起的原因,学界多有论述,结论大致如下: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直面戏剧作家们,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后冷战时期多边战争的爆发、民族矛盾的升级、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他们以挑衅的姿态把种种私密、污秽、暴力的场景搬上舞台,呈现人类精神崩溃的真相,迫使人们进行反思。就整体状况而言,对于造就了直面戏剧的社会现实,“同住地球村”的中国90后也许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不可能浑然不觉,反倒是具体作品中涉及的历史背景,有可能造成中国观众的理解困难。譬如说,不了解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恐怕不会发现《丽南山的美人》对现实的诸多隐喻;不熟悉佩克姨夫的成长经历,大概也很难洞彻《那年我学开车》中不伦之恋的内在原因。如果剥离掉特定的文化语境,在最浅显的故事层面,观众们直接接收到的又是什么呢?一个备受折磨的女儿企图摆脱纠缠不休的母亲(《丽南山的美人》),两个需要慰藉的灵魂陷入一场长久羁绊的畸恋(《那年我学开车》)。在鼓楼西排演的外国剧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突然崩溃的婚姻(《婚姻情境》)、无法沟通的夫妻(《早餐之前》)、渴望“盟友”的女孩(《奥利安娜》)、环环相扣的背叛(《背叛》)。这些作品的情感内核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亲密关系。《枕头人》和《审查者》的情况稍显复杂,前者有着极其丰富的阐释空间,后者首先关乎政治批判。但在导演周可眼中,这两部戏都与家庭生活紧密相关。回顾自己的剧目选择时,周可说:“一个阶段,我对‘童年阴影和原生家庭’充满兴趣,于是就有了《枕头人》和《审查者》。”[9]
(《那年我学开车》2017年演出海报)
(《婚姻情境》2021年演出海报)
不可否认,排演直面戏剧体现了鼓楼西生产精英文化的追求,但在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语境的漂移转换必然伴随着原信息的流失和新信息的汇入。鼓楼西的年轻观众,正从未成年走向成年,从校园走向职场,在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有太多事情令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渴望亲密关系,但身处亲密关系之中时,往往又会手足无措,甚或狼狈不堪。他们接受鼓楼西的直面戏剧,与其说是因为抽象的全体人类命运,不如说是因为具象的自身生存境遇。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鼓楼西自成立以来一直头顶着“直面戏剧”的标签,却从没排演过直面戏剧领军人物萨拉·凯恩的任何作品。原因很简单,鼓楼西不需要通过极致的舞台意象和尖锐的道德叩问来惊醒大众,它所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化和都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症候。当然,这种回应是严肃的,传递着创作者的现实思考和忧患意识。
02
中国本土原创:
重读经典、青年扶持与主流商业制作
鼓楼西排演的外国剧目,除《早餐之前》进行了大幅扩写、《枕头人》调整了几场戏的顺序外,余者皆忠实于原作文本。这些作品都试图揭示为日常生活表象所遮蔽的内心隐秘,就剧作文本而言,具有某种一致性。但鼓楼西与不同的导演合作,保证了二度创作的风格多元。鼓楼西自制的十部外国戏由七位导演执导,其中既有中国戏剧院校培养的周可、张慧,也有接受海外戏剧教育的张彤、陈洁、李迈(美国导演);既有初出茅庐的“少壮派”祖纪妍,也有由剧作家转型的“老一辈”过士行。他们的创作各具特色,浇灌出不同艺术个性的舞台形象。
鼓楼西排演本土剧目的情况则大相径庭。迄今为止话剧属于中国戏曲吗,鼓楼西只制作演出过三部本土剧目。2014年,以《枕头人》首战告捷后,鼓楼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接连推出《雷雨》和《五人间》,但都只演出了一轮便偃旗息鼓。再次出手,就是2018年的大制作《一句顶一万句》。四年之间,鼓楼西对待本土剧目的态度和思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雷雨》《五人间》《一句顶一万句》,这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排演路径:重读经典、青年扶持与主流商业制作。
最初,鼓楼西有着中西方戏剧经典“两条腿走路”的明确规划,按照李羊朵的说法,鼓楼西“选剧以中西方经典作品为主,重新解读、重塑经典”[10]。鼓楼西排演《雷雨》,就是要重新解读这部中国现代戏剧的扛鼎之作,寻求与当下观众的共鸣。当时,北京人艺《雷雨》笑场一事还未发生,但鼓楼西已经自觉把挑战传统演剧模式当作目标。李羊朵说,“我看了很多种版本的《雷雨》,可是大家的演绎都带着人艺味儿,连‘起范’都是一样的”。这让她很不满足,“制作一出不同的《雷雨》就让她念念不忘”。[11]邀请瑞典导演马福力( )执导,大概是想通过异于中国文化的他者视角,赋予《雷雨》新的时代精神和美学意蕴。马福力导演的这版《雷雨》大胆颠覆了曹禺原作,首先是以四凤的视角重新架构全剧──四凤的鬼魂重回周公馆,往事历历在目,但却融入了四凤的主观感受。如此改写,马福力的理由是,“以四凤为审视者,这其中有着女权主义的视角,也有底层阶级的视角,更有着浪漫爱情的视角”[12]。其次是取消了周朴园的实体形象,把他“在剧中的权重分布到戏剧场内的各个角落──他虽然人不出现,却是其他人物摆脱不掉的压力和阴影”[13]。马福力对《雷雨》动的两个大手术,单看哪一个,都不失为重构《雷雨》的可行方案,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矛盾。曹禺的原作中,四凤和周朴园并无太多瓜葛,周朴园从未像逼繁漪喝药那般给四凤以直接压迫,周朴园成为弥漫于整个周公馆内的超现实存在出自四凤的视角,便显得不甚合理。不过,艺术上的得失成败见仁见智,对话并挑战经典的尝试理应得到肯定和鼓励。唯其如此,经典才能避免沦为彼得·布鲁克所说的“僵死的戏剧”。只可惜,鼓楼西对中国戏剧经典的实验探索,《雷雨》之后即戛然而止。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鼓楼西排演本土剧目的第二种路径也过早夭亡。鼓楼西成立后发起“青年原创戏剧扶持计划”,计划每年“投入30万元,用于青年原创戏剧作品的发掘与培养,通过推荐及自荐等途径,面向全国收集优秀青年原创话剧作品,经过筛选,每年选取1至3部优秀作品,进行剧本购买及商业制作演出”[14]。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草草收场,只留下了一部作品──《五人间》。
《五人间》最早上演于北京大学剧星风采大赛,由当时就读于北大中文系的大四学生曾伟力编剧导演。“剧星”是北大学生会主办的颇具影响力的校园戏剧活动,每届比赛持续一学年,秋季学期举办初赛,春季学期举办复赛和决赛。近几年,时有“剧星”作品走出北大演出[15],但出售版权、交由专业团队制作、完全面向市场演出,至今还只有《五人间》一部。《五人间》参加“剧星”初赛时,被担任评委的裴魁山看中,推荐给了鼓楼西。能在一众“剧星”作品中脱颖而出,说明《五人间》的剧作有其过人之处并且蕴含着一定的商业潜力。不过,相比艺术上的价值,鼓楼西排演《五人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搭建从校园戏剧到专业制作的桥梁,探索青年原创作品孵化的可复制经验。在这一层面上,鼓楼西彻头彻尾地失败了。鼓楼西的排演没能让《五人间》更上一层楼,反而削弱了学生演剧的青春锐气。
重读经典与青年扶持两条道路的中断,令人唏嘘。当然了,鼓楼西不是这两种排演路径唯一的实践者。于前者,以《茶馆》为例,李六乙和孟京辉分别于2017年、2018年导演了两版极具个人风格的《茶馆》,王翀则与中学生合作,在校园里演出了《茶馆2.0》。《茶馆2.0》只进行了内部演出,李、孟两版《茶馆》毁誉参半,孟版《茶馆》还引发了包括退票风波在内的种种争议,显示出向经典发起挑战的任重道远。于后者,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以及很多机构组织的剧本征集、青年培养计划,均在不同程度上抱有孵化青年原创作品的目的,尽管也推出了一些口碑之作,却没有积淀下比较成熟的孵化模式。这些现象表明重读经典和青年扶持面临着诸多掣肘,隐约透露出鼓楼西“知难而退”的部分缘由。
鼓楼西排演本土剧目遭遇挫折,李羊朵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剧本荒──“国内的剧本,如果有合适的,我是不想放弃的,但这可能得靠机缘”,“国内的剧本很多都是大部头,动辄十几个演员,适合小剧场演出的比较有限”;二是鼓楼西作为制作单位的不成熟──“做孵化培育和做《枕头人》那样的成熟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16]两个理由,后者比前者更具说服力。仅论近年来的小剧场创作,原创乏力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我是月亮》《驴得水》《蒋公的面子》等佳作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在当今可供上演的中国戏剧经典固然有限,却也不乏《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这样的成功案例。以上作品的创作背景情形各异,成功原因也不尽相同,恰恰说明了排演本土剧目潜在的多种可能性。鼓楼西实践受挫,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找准市场定位和目标观众,无法形成剧目选择—排演制作—市场营销的稳定模式。
(《一句顶一万句》2019年演出海报)

2018年,鼓楼西剧场把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搬上戏剧舞台,开启排演本土剧目的全新路径。《一句顶一万句》首演于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是鼓楼西首部大剧场作品,也是鼓楼西首部大规模全国巡演的作品。与《雷雨》《五人间》相比,鼓楼西排演《一句顶一万句》时最根本的转变在于对市场定位和目标观众的判断──这是我称其为鼓楼西“主流商业制作”的最主要原因,所谓“主流”,指的是鼓楼西意在吸引此前不看戏或很少看戏的观众走进剧场:“大剧场的观众群体和小剧场不同,他们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不会有那么高的要求,他们更需要的是共情。”[17]牟森导演的重出江湖能在业内掀起波澜,刘震云对孤独体验的捕捉能唤起普遍的生命情感,但原作IP的巨大影响力才是保证此剧“出圈”的关键。
鼓楼西进军大剧场是为了谋求发展突破。在选择大剧场的剧目时,李羊朵首先考虑的就是改编中国文学经典(主要指小说),因为很多小说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认知度,而“认知度意味着受欢迎程度”[18]。改编小说经典与重读戏剧经典,二者各有各的难处,但前者可供“打捞”的范围更加宽广。《一句顶一万句》之后,鼓楼西正在筹备改编刘震云的另一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2020年,网剧《隐秘的角落》热播,鼓楼西趁势拿下原著小说《坏小孩》以及原著作者紫金陈另外两部小说《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的舞台改编权。这些作品,构成鼓楼西大剧场的IP改编序列。另一序列来自小剧场到大剧场的“升级”。2019年,鼓楼西在小剧场版本的基础上制作了大剧场版《枕头人》,目前还计划排演大剧场版《安娜在热带》。这两类大剧场剧目,第一类自然依托原作IP的影响力,第二类则借重小剧场版积攒的人气。小剧场以精英视角守住基本盘,大剧场以大众面向拓展观众群,构成鼓楼西运营发展的“双轮驱动”。
此外,鼓楼西还将在小剧场排演全新版本的《我是月亮》,这或许会成为鼓楼西综合了重读经典和青年扶持的第四种排演路径──打造中国原创戏剧新经典。依目前的势头来看,未来鼓楼西本土剧目全面出击、多点开花,并非痴人说梦。
03
都市文化空间:始于戏剧,不止于戏剧
最早涉足戏剧行业时,李羊朵并未打算经营剧场。在寻找演出场地的过程中,她发现,北京可供体制外戏剧团队进行演出的剧场十分稀缺,国话先锋剧场、朝阳9剧场等有限的几个选择,排期也很拥挤,这让她产生了新开一家剧场的想法。最终,她租下当时已经很少被使用的全总文工团排练厅,将其改造为鼓楼西剧场。从基本闲置的院团场地到充满活力的民营剧场,鼓楼西的前世今生,为如何有效利用国有资源提供了有益启示。
除上演自制剧目外,鼓楼西还出租剧场,上演了大量场租剧目(包括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南锣鼓巷戏剧节等戏剧节展的部分剧目)。这一方面是由于鼓楼西的自制戏数量有限,无法做到全年不间断演出自制戏;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北京的大量体制外作品对剧场有着迫切需求。据我粗略统计,成立六年以来,有超过110部场租剧目于鼓楼西上演,其中约有15部作品演出了不止一轮。鼓楼西和一些创作团队稳定而长久的良性合作,有助于这些团队的可持续性发展。一些优质剧目的反复上演,对剧场整体风格的塑造、知名度的提升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极具人气的演员王子川不仅出演了鼓楼西的自制戏《枕头人》,他导演并主演的《非常悬疑》《雷管》《雅各比和雷弹头》也都曾在鼓楼西上演,“王子川喜剧”由此成为鼓楼西的招牌之一。2020年苏州举办的第三届江南青年戏剧节,在“城际交流精品剧目汇演”板块,鼓楼西除带去“鼓楼西经典剧目”《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还带去了“鼓楼西特邀剧目”《非常悬疑》《杏仁豆腐心》《窦娥》,而《窦娥》尚未在鼓楼西演出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鼓楼西无论作为戏剧制作单位还是作为剧场运营单位,其实力和影响力都得到了外界的认可。
采取“场制合一”的经营模式,既上演自制剧目,又上演场租剧目,鼓楼西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剧场。民营的繁星戏剧村、国有的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都兼演自制剧目和场租剧目,在这一点上与鼓楼西没有本质差异。但鼓楼西举办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足以与其他剧场拉开由量变到质变的距离,显示出鼓楼西不满足于戏剧演出场所和戏剧制作单位的定位而是要成为“都市文化空间”的诉求。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认为,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9]。剧场的空间实践( ),除了戏剧演出时的“表演”与“观看”,显然也包括发生于剧场内的其他公共活动。鼓楼西位于北京北二环内的小八道湾胡同,从最近的地铁站走来,要在胡同里穿行约十分钟。全总文工团院内栽种着树木和爬山虎,颇有闹中取静之意。剧场还开设有咖啡厅和名为“樱桃园”的书店。雅致的环境与鼓楼西的文化活动相得益彰,生产出带有诗意栖居意味的新空间。
这些活动,有些与戏剧密切相关,如2015年8月,鼓楼西联合波兰驻华大使馆举办“波兰戏剧文化月”活动,“影像单元”放映了两部戏剧电影《行李箱》《瓦莲京娜》,“剧本单元”则呈现了《阿波隆尼亚》的剧本朗读,成为一年后华沙新剧团在中国演出该剧的先声;有些与戏剧没有直接关联,但同样彰显着鼓楼西的文化品格,如2019年10月举办的莫言和勒·克莱齐奥对谈活动、2017年1月举办的罗马尼亚诗人埃米内斯库《金星》长诗分享会等。鹦鹉泼水节和鼓楼西朗读会是鼓楼西长期举办的两项活动,前者于2017年停办,后者于前者停办后开办,至今仍在定期举办,并以大咖云集的朗读阵容成为鼓楼西的品牌活动。

(鼓楼西朗读会,史航,朱朝晖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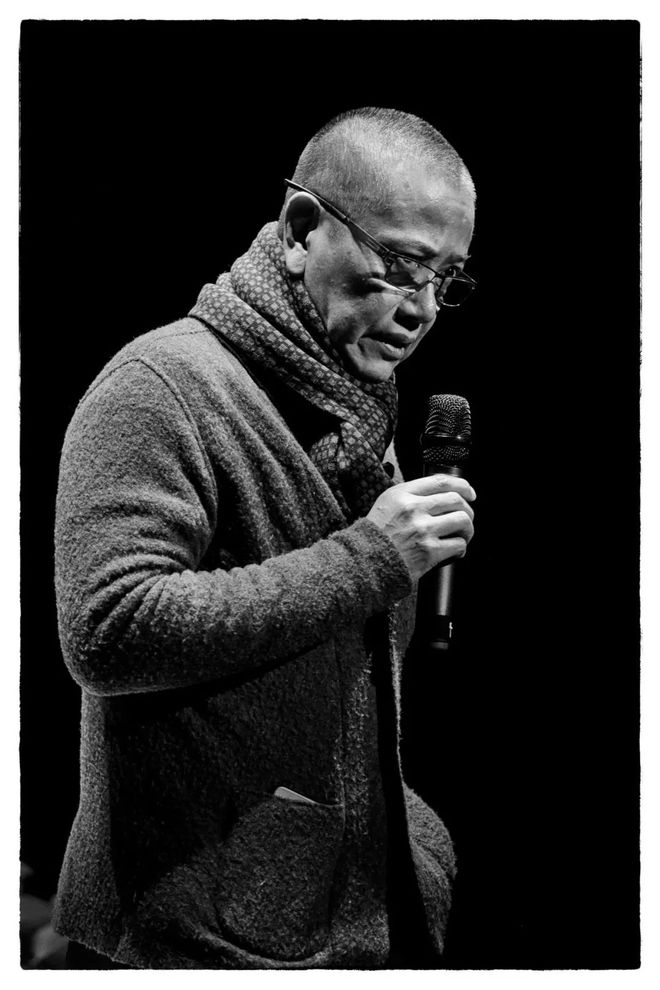
(鼓楼西朗读会,陈丹青话剧属于中国戏曲吗,朱朝晖摄影)